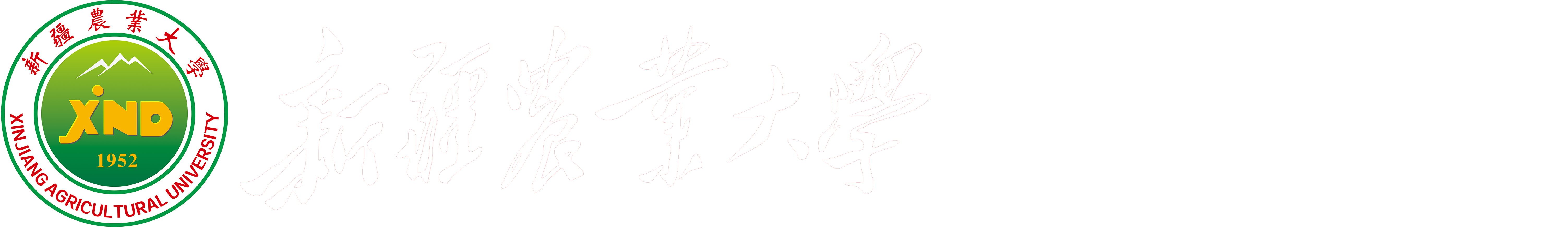参加几期“回归经典”读书会后,逐渐有了一些感悟。尤其是马克思政治哲学这一期,主题是讨论犹太人的“金钱”拜物教。

初次接触马克思的《论犹太人问题》,萦绕在我脑海的首先是一种困惑:为何马克思要花费如此大的力气去批判鲍威尔?随着交流与阅读的深入,我才恍然:马克思在此役中真正要击碎的,不仅仅是一个论敌的浅薄之见,更是整个现代政治所构建的、关于“自由”与“解放”的神话。他犹如一个冷静的解剖师,剖开了“政治解放”这具看似完美的躯体,向我们揭示了其内在的、无法自我愈合的裂痕。
马克思的核心洞见在于,他清晰地区分了“政治解放”与“人的解放”。鲍威尔要求犹太人放弃宗教以获得公民权,在马克思看来,这恰恰是将问题局限在了“神学”的牢笼里。他指出,现代政治国家(通过革命)从国教中解放出来,实现了政治解放,但这只是一种有限的、矛盾的解放。国家在政治层面宣布无视私有财产、教育、出身,但在现实的市民社会中,这一切却大行其道,成为真正的主宰。于是,人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:在天国(政治共同体)中,他是想象的、平等的公民;在尘世(市民社会)中,他是现实的、利己的、被私有财产所分割的个体。
正是在这里,马克思完成了他最精彩的理论跳跃。他将“犹太人问题”从一个特殊的民族宗教问题,提升为一个普遍的现代性问题。他指出,犹太精神的世俗基础是“实际需要,利己主义”,而它们的世俗崇拜偶像便是“金钱”。因此,“钱是以色列人的妒忌之神;在它面前,一切神都要退位。”